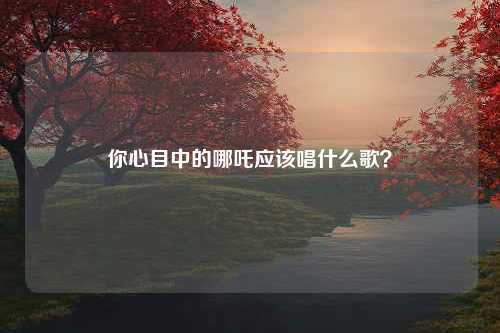时光荏苒,屡变星霜。教师节又到了,我写下一张明信片,郑重地投进大雁塔地铁站F口的墨绿色邮筒里,寄给远方老家乡镇政府的堂曾祖父——我的启蒙老师。在这个电子通讯十分便捷的年代,除了一些去旅游景点玩儿的文艺青年偶尔买张明信片,估计没有谁会想起干寄明信片这种“老掉牙”的事儿了。而我就是那个怀旧守拙的例外吧。
现在的孩子们压根不知道“民办教师”是什么意思,毕竟他们离上个世纪那段艰苦岁月已经稍稍有些远了。民办教师的历史渊源挺久的,早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上世纪50年代开始,全国教育事业才刚刚起步,底子薄、基础差,教育水平落后、教师缺口很大,特别是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薄弱。国家实在没办法,就想出聘请雇佣“民办教师”的折中办法来缓解现实矛盾——给农村学校就地在本村找一些有一定知识水平的农民来当“临时工”老师,俗称“民办教师”,简称“民教”。他们没有固定的正式编制,因此工资薪酬很低。但是在淳朴的农村,乡亲们普遍尊重有文化的人,孩子们也不管老师是正式编还是临时工,只要教得好、对待孩子好,学生们自然喜欢和敬重。所以,总体上民办教师比较受人尊敬,这也是很多民办老师拿着微薄收入、数十年如一日坚持下来当老师的重要动力之一。

民办教师也有机会成为公办正式教师,前提是需要参加考试并且通过才能转正。1981年是民办教师的分水岭,从那以后国家就不再大规模招民办教师了。之前没有考过的民办老师,以及1981年以后担任民办教师的统一叫“代课老师”,即代理上课的老师。有极少部分代课老师最后幸运搭上当地政府“民转非”的末班车,考试成了公办老师,退休以后还有退休金。但是绝大多数代课老师至始至终都没能转正。
关于民办教师、代课老师的文学、影视作品很多。比如,得了茅盾文学奖的《天行者》就是专门写乡村民办代课老师的故事,特别感人。路遥的代表作《人生》《平凡的世界》里边的主人公高加林、孙少平高中毕业回农村老家之后,都当过村里的民办教师。张艺谋导演的《一个都不能少》中的魏敏芝、倪萍主演《美丽的大脚》中的张美丽,还有孔笙导演的火爆扶贫电视剧《山海情》里边的白老师,统统都是民办代课老师。他们平凡普通,却坚韧不拔,手把手教出来无数个农村娃,也在文学影视作品中感动振奋了无数人。
我的启蒙老师也是一位白老师。我出生在1989年,是一个“80后不认、90后也不要”的人。1996年,我在村里小学上了学,那时候没有幼儿园、学前班一说,都是直接上一年级。学校里除了校长之外,全部都是民办代课老师,我的班主任、启蒙老师是村里一个20岁出头的年轻小伙儿。那时候,他高中毕业没几年。白老师虽然年轻,但是辈分很高,是我的堂曾祖父,我得管他叫太爷爷,不过我从来没叫过。
刚上学的时候,村里的小学就只有几间土坯房,几间大的做教室,老师们在一间小的里集体办公。学校连厕所都没有,临时在学校背后不远处的两户人家借用厕所,女生向左、男生往右。说是厕所也只是巴掌大点的土圈,男生们嬉笑打闹着围着灰堆、土墙比谁尿的高,经常惹得主家老汉呵斥喊叫。不过第二年旁边新学校就建成投用了,两排阔气的楼板房宽敞又明亮,成了全县西片学区的中心学校。不久,土坯房老校舍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变成了大操场和一排厕所。
开学第一课,白老师先教我们如何用小刀削铅笔,他小心翼翼地示范指点,生怕一帮碎娃娃操作不当、割了手指。班里有个小弟弟当时虚岁才六岁,还穿着开裆裤就被他爸送来上学,几个调皮捣蛋的同学课间还欺负嘲笑他。白老师当天就去家里和他爸沟通,第二天小弟弟就不再穿开裆裤了。由于他年龄小,个头没长起来,上讲台考默写生字手都够不到黑板,白老师干脆抱着他写生字。
白老师是我们这帮小屁孩儿的全能老师,不光是班主任,语文、数学、书法、体育、自然、思想政治、音乐美术都要教;不光是我们班,他还要承包其他年级的体育课。有意思的是,学校体育课以及六一儿童节汇演、运动会等排练体操队形,用的黑色塑料口哨都快成古董了。白老师说他上小学的时候就用的这个黑口哨,如今他当了代课老师还得用这个黑口哨。虽然口哨是塑料做的,但声音清晰嘹亮、特别好用,只是口哨下沿已经被长期使用、咬掉了快一半。
语文课上,白老师教我们识字、写作文,经常分享一些好词好句好片段。我到现在都记得《难忘的一件事》的一个好开头:“这件事,就像平静的湖水里投入一粒石子,泛起一片涟漪……”音乐课上,白老师先给我们教一些《小二郎》《卖报歌》《春天在哪里》这样的儿歌,后来又教国歌,再后来教《让我们荡起双桨》《明天会更好》。美术课是白老师的短板,有一次他实在没辙,就在黑板上用粉笔画一个简陋的罐子,让大家照着画。二年级以后,每周二、周四会有一节书法课,白老师教我们握毛笔、舔墨,让大家把白纸蒙在字帖上临摹练字。有一次我忘带字帖了,又舍不得去学校门口小卖部花两毛钱新买一张,毕竟是两根辣条的钱,索性直接在白纸上随意乱写。白老师发现后很生气地说“你连走都不会,就想直接跑了!”我十分惶恐惭愧,白老师却扭头出去了。过了一会儿,他回来教室手里拿了一张字帖递给我说,“凡事都有章法规矩,做事要有耐心恒心”。这句话,我到现在都刻在心里。
白老师手把手带了我六年,期间我垄断了班里的第一名,还经常在全乡乃至全县西片学区会考中拿第一名,奖状、荣誉证书攒了一厚摞,给白老师争了气,所以他特别喜欢我。有一次村里人结婚过事,白老师罕见地喝醉了,当着村里很多人的面,指着我骄傲地说:“这是我的得意门生”。我也特别感恩遇到这样一位启蒙老师,他不光教我们学知识,还带我们看见更大的世界。他办公室角落有一个很大的纸箱,里边有攒下的期刊杂志、故事书、花娃娃书(小人书、连环画),我最喜欢送作业的时候蹭书看。我记得很清楚,借的第一本书是《杨靖宇的故事》,小小薄薄的书,泛黄的书页,生动感人的故事,伟大坚韧的杨靖宇将军,着实震撼了我幼小的心灵。后来白老师把这本我最喜欢的书送给了我,直到现在这本《杨靖宇的故事》还在我的书架上放着。
那时候村里的老师都是半农半工,家里都种着地,兼职代课当老师。每到秋收季节,我们这些学生娃的苦日子就到了——要给老师义务劳动收地。庄稼一熟,学校就停课了。第一天,各班老师要组织本班学生先分头到校长家的地里收庄稼,之后才给老师们收庄稼。不管是掰玉米、拔黑豆、拔荞麦、捡土豆,全部都是纯手工,没有手套、也没有镰刀等工具。最恶心的是我姐的班主任,他家里地很多,动辄种几十亩上百亩的玉米,全校学生年年都得去给他家、他大哥二哥家义务劳动掰玉米棒子,干一整天连口水都喝不到。
白老师家里地不多,也不让学生义务劳动,只让同学们干过一次农活——“间”向日葵。
陕北春天干旱少雨,还有野兔、沙跳(一种弹跳能力很强的野鼠)吭食庄稼幼苗,于是农民播种的时候为了确保苗够,就多撒一颗种子,苗长出来的时候同一个位置会有两棵向日葵苗,等长到二三十公分高的时候,就需要剔除拔掉多余幼苗,只留下一棵好苗子作为“种子选手”,这个过程就叫“间苗”。“间”庄稼苗是苦最轻的农活,白老师放完学才叫我们帮他“间”向日葵。
大家一字排开,每人负责一行向日葵,轻轻松松走一来回就完成了。回到村里,白老师让大家在他家集合,给每人发了一个作业本、一根铅笔作为劳动报酬。还有一次,班里给校长收完荞麦,回来路上碰到一个村民在收黑豆,他央求白老师让大家帮他拔黑豆。白老师征求了大家意见,然后和村民谈判博弈——每人2元钱。人多手稠,不到半小时我们就拔完了,一手验工、一手发钱,双方皆大欢喜,而白老师却没有拿钱。
四年级的时候,村部维修后墙外剩了一堆砖头,村支书让校长安排学生搬到另外一个地方,校长命令我们班去搬。陕北春天经常刮风沙,当天恰好刮起沙尘暴,刮的昏天暗地,能见度很低。大家都缩着脖子、低着头抱着砖来回跑,着急搬完回教室,眼角、嘴角、头发里都是沙子。慌乱中,有个同学和我撞了个满怀,我的左眼角撞到了对方怀里砖头角,当场就流血了。白老师接到报告,赶过来叫停了搬砖,又找校长据理力争,让村上找几个村民搬。还把我带到办公室仔细洗了伤口、涂了药。放学回家,我妈看到我眼角破了很心疼紧张,生怕脸上留了疤,不好讨媳妇儿,就讨了土偏方用白芝麻捣碎了敷在伤口。再后来村上、学校使唤我们班同学义务干重活、危险活,白老师就坚决拒绝、一顶到底。
六年级的时候,班里男生突然流行起“耍钱”。一些同学从家长那里学到了的恶习,在班里用骰子“摇单双”卖宝让大家,或者弹“钢镚儿”猜“字”还是“面儿”的一面(正反面)。没过多久,白老师就发现了这一恶劣现象。愤怒的他让所有参与过的男生在国旗下边站成一排,挨个扇了两个耳光,打完还要罚站半天,外加写保证书,赌咒发誓“再也不了”。
六年时光,弹指一挥。我们小学毕业了,白老师也遇到了职业生涯的重要关口。当时陕北地区农村生源不断减少,大中专高等院校的师范毕业生一批又一批分配到了农村学校,民办教师、代课老师也逐渐“穷途末路”。尽管绝大多数民办教师经验丰富、能力很强、威望很高,学生和家长们尊重爱戴,但在时代面前全部被“一刀切”下了岗,离开了心爱等课堂讲台,学校里全部换成了良莠不齐的公派教师。然而这些默默无闻的代课老师中,有的人已经奉献了全部的青春年华,到了失去了重新学习一门安身立命的技术的年纪,一些人无可奈何地回归土地,重新当起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还有一些人,背井离乡出门打工挣点辛苦养家钱。
发自内心的喜欢和热爱教育事业的白老师选择了另外一条更艰难的路。一穷二白的他抱着女儿、领着同是民教的妻子,拖家带口在县城找了个私立民办小学继续教书,租了间民房、交了房租的他兜里只剩下36块钱,捉襟见肘的日子就这么咬牙熬着。三年后,陕北九年义务教育普及力度不断加大,县城里私立民办学校也纷纷倒闭了。白老师又失业了,但生活的打击磨难并没有让他灰心丧气、“躺平”“摆烂”。他重新燃起斗志,克服了重重困难,办起了幼儿园,继续奋战在教育战线上。他对学习进取保持着高度热情,还逼迫自己拿到了陕西师范大学的本科学历。
幼儿园慢慢步入正轨,有了稳定的生源和师资力量,白老师处理各种事务也越来越得心应手了。2018年,村里换届选举,白老师积极参加竞选,成功当选了村主任,却也忙的四脚朝天、焦头烂额。不过担任村干部的这段履历,让白老师受益终生。因为陕西省有从村(社区)干部、优秀工人、劳模中考录公务员的优惠政策,这给白老师的职业生涯带来了重大转机。不过好事多磨,没有人能随随便便、顺顺当当成功,从报名考试开始白老师就面临着极大困难。一般招录公告规定报名考试者年龄必须是45周岁以下,原本白老师完全符合条件。但这类报名和国考、省考公开报名不同,而是采取层层筛选、组织推荐的方式,村(社区)、乡镇(街道)先推荐,然后县委组织部圈定范围、分配指标、最终上报,所以县上的态度很关键。
当时县上推荐了两个年轻村干部去考试,白老师被刷掉了,给出的理由是“年龄逼近45周岁”。他不甘心也不服气,反复就年龄限制这一条额外“土规定”和县上沟通、争取、甚至争执,最终争夺到了十分珍贵的报名考试权。尽管笔试他在本岗位排名第三,上岸希望十分渺茫。但教师出身的他,气质沉稳、思维敏捷、口才很好,普通话也标准,加上准备极为充分,他在面试中取得超高分数,强势逆袭翻盘,成功冲顶成为第一名,最终在45周岁前压哨考上了乡镇公务员。上岸后的他,服从分配到乡情复杂、民风强悍的C镇入了职。白老师对农村情况熟悉、经验丰富,电脑操作娴熟又任劳任怨,而且像精准扶贫、疫情防控、大棚房整治、宅基地腾退这些棘手复杂的工作,他都能兢兢业业干好。平时说话办事接地气,老百姓也服气他,村上的农民群众大事小事都愿意给他打电话。俗话说功不唐捐,工作表现突出、群众基础很好的他,成了镇政府驻村干部中的标兵,镇上领导评价他“坐下能写、站起能讲、出去能干”,老百姓和他“称兄道弟”把他当自己人。
从工资微薄的代课老师,到白手起家的幼儿园园长,从焦头烂额的村主任,再到“六边形战士”的乡镇公务员,年近知天命的白老师,在生活的各种夹击摩擦下,硬是闯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人生之路。他把“功不唐捐、相信希望”当做自己的人生信条,他明白“一件事情不是有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下去才有希望”的道理,他始终相信“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可能。
那个起点低微的农村寒门青年,那个曾经手把手教我们数数认字、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的启蒙老师,也把“日拱一卒、坚韧不拔”的意志品格传导给我们。因为他,我们的字典里没有随随便便“放弃”两个字。我总是很感恩,在对世界懵懂无知的小时候,遇到这样一位普通平凡却具有人格魅力的启蒙老师,我想这就是老师这个职业的伟大意义所在。毕竟,老师教给孩子的不仅仅是知识或技能,更是在孩子心中塑造一种精神品质,能够让我们泰然自若,与自己的时代狭路相逢,勇敢地面对生活中的一切!